对圣经中译本的省思与展望
2020-11-23 08:47 纳爵之盾 阅读量:12831
一 中文圣经译文现状
圣经译为中文,一方面方便了华人基督徒的应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语言文字演变的「域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中文「提供了走出自我封闭、拓展自身的新机运、新参照和新内容,提供了饱含现代意义的语言文字变革途径。」[5]圣经中译尤其为很多方言和除汉族外某些民族语言的文字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
中文圣经翻译特色。纵观所有中文圣经译本,可以看到下列几个特色:
1、在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上,天主教选择了拉丁通行本(Vulgata),这是当时教会通行使用的语言,直到思高圣经译本才转为由圣经原文(希伯来文、阿拉美文和希腊文)进行中译。
2、翻译者最初都是外籍传教士,中文并非他们的母语[7],他们的译本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
3、在所使用的语言上,最初多为文言文(深文理)译本,再到浅文言(浅文理)译本,最后到白话文译本,当然也不能忽略还有很多方言译本。
4、从事翻译工作的,有个人也有团队。
中文译本虽然众多,但至目前为止,在华人领域最具权威的两个译本,一是天主教的「思高圣经」,一是基督新教的「和合本」。
思高圣经的翻译,先由意大利方济会士雷永明神父(Gabriele Allegra,1907~1976)于1935年一人开始,后与几位中国神父创立「思高圣经学会」(1945),继续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968年第一版圣经完整版问世。其后多次再版,现最新版是2015年纪念思高圣经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版,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订版。思高圣经学会在第一版的序言中详细介绍了其译本所选择的原文文本及理由。这是迄今为止,在天主教所有译本中,一本真正依照圣经原文文本翻译的中文版本,而且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人完成的,即便选取原文的理由和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有关《德训篇》的翻译,虽然主要译自希腊文,参考了当时考古发现的希伯来文残卷,同时亦保留了拉丁通行本所多出的词句(以楷书体排印);而且全书的章节,同样是以拉丁通行本来划分。
按思高圣经学会同仁的看法,这是尊重教会在历史中一直使用拉丁通行本的习惯;但问题是,当有人参照阅读别的版本时,则带来很大的困扰。例如,同为天主教译本的法文La Bible de Jérusalem和英文New Americain Bible的《德训篇》则都是选用希腊七十贤士译本作为底本,而且章节也完全相同。
基督新教的和合本圣经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经历可谓曲折。由最初的「圣经唯一,译本则三」,指当时的文言文(深文理)、浅文言(浅文理)和官话(白话文)三个译本,而且还分「上帝」版和「神」版,最后「官话和合译本」(1919)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行,直到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后简称「和合本」,是基督新教广为使用的译本。
这个译本的起源也是来自外国传教士,但翻译过程中也有中国基督徒的协助。「和合本」随英语修订版圣经(English Revised Version)所使用的原文底本。它的出现赶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直译为基本翻译方式的白话圣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白话文的提倡者和实践者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许地山、林语堂、田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老舍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圣经的语言。」[8]
联合圣经公会于1983年计划修订「和合本」,1984年制定根据原文并参考其他译本的修订原则,并力求以通顺自然的中文来表达。1985年在台湾展开修订工作,2000年完成新约,并从这一年开始,联合圣经公会将「和合本」的修订及出版交给香港圣经公会,2010年全部竣工,出版整部新旧约全书。[9]此修订版的一大特色,是由以中文为母语的圣经学者完成的。

二 以法文TOB和BEST为例
TOB是Traduction Œcuménique de la Bible(圣经大公译本)的缩写,是包含各基督宗派的法文版共同译本。[10]
TOB的创意由来已久,法国神父Richard Simon[11](1638~ 1712)在十七世纪时,已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施。直到廿世纪天主教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受《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1965)的鼓励,这个想法再次浮出水面。由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圣经教授主导,邀请各基督宗派的圣经学者参与。
开始时,因为只有两位东正教圣经学者参与,所以在TOB第一版(1975)和校正版(1988)中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圣经纲目所包含的书目,直到2010的修订版才加入了东正教圣经纲目中的书目(《玛加伯》卷三、四;《厄斯德拉》卷三、四;《默纳协的祈祷》;《圣咏》一五一)。也在其首页标明了构思、编辑及协调者的名字,共计40位;参与翻译者的名字,共计114位;同时,也标明了译者们所使用的原文版本圣经。在序言中也详细讲述了这一宏伟工程的产生及所经历的过程。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这的确是首创,并且意义非凡。[12]因为基督徒的分裂始于对圣经的不同见解,而能够共同翻译注释圣经,则是走向合一的康庄大道。
由于TOB翻译的质量,及其所持守的翻译原则,让这本圣经成为法语界圣经学者最多使用的译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超越了所有至此现有的法文翻译」[13]。
BEST是La Bible en Ses Traditions(传承中的圣经)的缩写。在了解BEST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它的前身:《耶路撒冷圣经》(La Bible de Jérusalem)。由耶路撒冷圣经及考古学院负责翻译,先是于1948年到1955年以单行本发行,于1956年出版第一版完整本。参与翻译的共计33位(圣经首页标有他们的名字),其中包括道明会士、耶稣会士、本笃会士等等,都是当时法语界最为杰出的圣经学者。1977年出第二版修订版,1998年出第三版修订版,其翻译质量从开始便得到世界公认。第一版发行后很快就滋生了英语版的Jerusalem Bible(1966),其译本、导言和注释都是按法语的耶路撒冷圣经版本。[14]
进入第廿一世纪后,耶路撒冷圣经及考古学院意识到再版其圣经的必要性,而这次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尝试,就是自2010年所开始的BEST计划。如果说圣经翻译本身就是诠释的话,那么BEST想呈现给读者的,则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包含从圣经文本诞生之初,它所经历的诠释过程,让圣经文本和教会的生活传统做完美的连接。
它的另一特色是数码形式,并且是合作参与的模式,邀请世界各地的圣经专家学者参与的。目前已开出29个注释栏,包括犹太文化、教父学、古代近东、考古学、礼仪、神学、古代与现代文学、艺术史等等,可以说种类繁多,因为这些都属于圣经的世界,构成了圣经写作和解读的大背景。
今日正是处于数码时代,重新构思多语种的圣经,可以有不同的尝试。出版圣经不能再满足于一个单一的语言版本,人们对各种原文版本的认知,让我们看到圣经经文本身的多元性。在不同的信仰团体中,这些版本的传承也让我们看到经文本身的生命力。不仅透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版本,也透过不同的神学著作、礼仪生活、文学作品、艺术创作等等,看到了圣经给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灵感和惊喜。
BEST的工程是庞大的,我们无法知道何时才是终点。但正如圣经文本的传承,我们也在期待中继续我们阅读和诠释的旅程。
看到法语版的TOB和BEST伟大工程,会给圣经中译带来哪些启发呢?
[1]本文节选自:崔宝臣,〈圣经文本问题探讨,兼论对圣经中译的省思与展望〉,《神学论集》204~205期(2020年夏),169~206页。
[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9)。
[3]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 49(香港:道风书社,2018)。
[4]介绍圣经中译历史的文章和著作也可参阅:Piet Rijks著,黎明辉、袁志雄、黄翠芬、陈翠欣译,〈圣经在中国的历史〉,《神思》89期(2011),73~102页;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圣经的中文翻译》,天主教研究学报,第二期(2011)。
[5]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61页。赵晓阳博士在专著中特别选了18个因圣经中译而进入中国的新词语做了分析,包括:耶稣基督、亚当厄娃、梅瑟、犹太人、耶路撒冷、乐园、十字架、福音、洗礼、先知、圣神、天使、五旬节、安息日、阿们、默西亚、撒旦、厄玛奴耳。
[6]参: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160~243页。
[7]学者们只有在介绍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译本时,提到有一位中国基督徒徐若翰(Jean Xu,?~1734)帮忙翻译圣经。参: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34~35页。而赵晓阳在提到徐若翰时称之为神父,参: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26页。
[8]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157页。
[9]参: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414~415页;蔡锦图,〈从《和合本》到《和合本修订版》〉,《神思》89期(2011),35~40页。
[10]我们在这里选择介绍法文版的大公版本TOB,并不排除其他语言版的大公版本,只是在同类大公版本中,法文版的TOB实为最杰出的。关于其他语言的大公版本,参:房志荣,〈新约全书「现代中文译本的来龙去脉」〉,《神学论集》26期(1976),609~621页。房志荣神父在其文中也称法文版的TOB为「精心杰作」,只是那时他还没有看到2010年TOB的修订版,否则他一定还会赞叹有加!
[11]宗座圣经委员会称之为现代圣经诠释的奠基人,参:Commission Biblique Pontificale, Interprétation de la Bible dans l’Eglise(Paris: Les Editions du Cerf, 1999), p. 28.
[12]Cf. Jean-Marie Auwers et collaborateurs, La Bible en Français,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Bruxelles: Lumen Vitae, 2002), p. 56.
[13]包智光(François Barriquand)著,陈嘉敏译,〈比较白、徐和马礼逊有关罗马人书1~4章翻译文本:新约合一译本的试验案例〉,《神思》89期(2011),16页。
[14]思高圣经中没有介绍是否参照法语版耶路撒冷圣经,但笔者猜测可能性很大。希望以后有人可以比较这两个版本,做这方面更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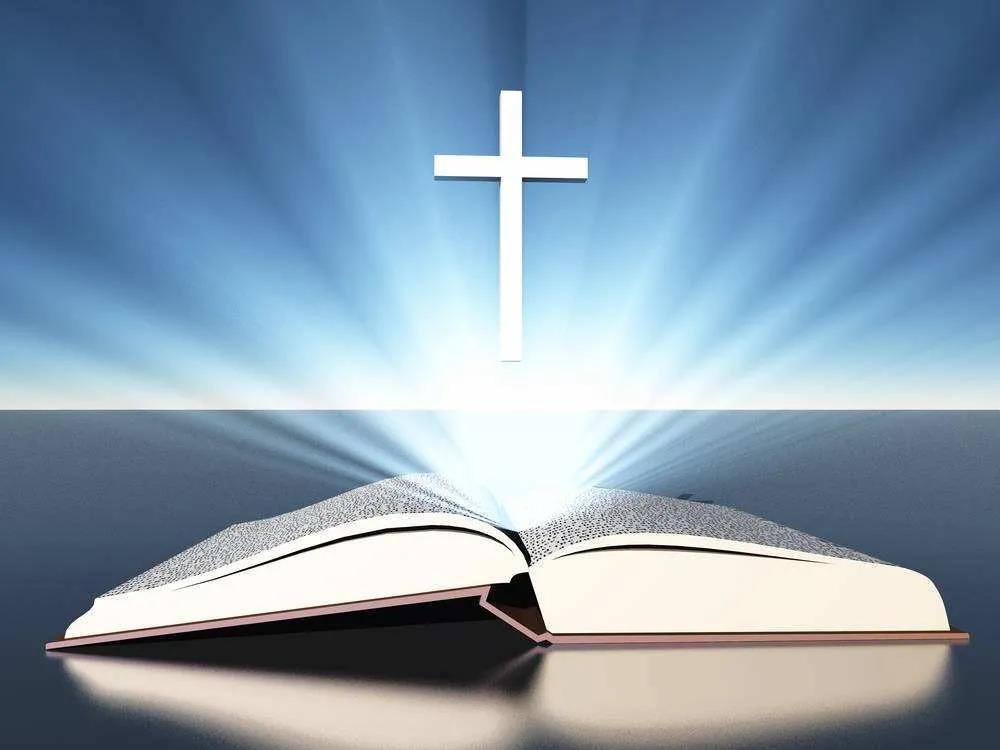
三 对圣经中译本的展望
01翻译本身
其实,对各种语言重要译本的修订,一方面是因为更多古代文献的出土,及对圣经原文的全面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每一种现代的生活语言,都在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化。基督新教的「和合本圣经」于2010年所完成的修订,就是一个好的范例。那天主教的「思高圣经」呢?
思高圣经学会当然已经意识到出版「思高圣经」修订版的必要性。其现任会长黄国华神父于2008年已经筹划并展开修订「思高圣经」的工作,而且是以新约开始。只是他提出新约修订版本的翻译原则时,其中两点颇令人费解。一是回归「思高圣经」初译时所规定的「信、达、雅」,以「信」为优先,其次是「达」和「雅」,而不再按照出版完整版时「信、达、雅」兼顾的修订原则。二是统一相同希腊文词语的中文翻译用词。当然这样的翻译原则容易达成「信」的标准,也给查阅圣经重要概念在某卷书中所使用的次数带来了方便。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语境,同一个单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修订工作以《费肋孟书》开始,在修订一章6节时,把原来的译文「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ἡ κοινωνία τῆς πίστεώς)尝试修改为「同一的信德」,理由是κοινωνία有「参与」、「分享」之意,思高第一版译作「慷慨」偏离了原意,而将ἡ κοινωνία τῆς πίστεώς译为「同一的信德」是为表达κοινωνία所包含的「共融、契合」之意。我们尚且不论这样的修改是否更符合原文之意,但κοινωνία固然在《费肋孟书》只出现一次,却在新约中共出现19次。例如斐2:1 中的「圣神的交往」(κοινωνία πνεύματος)该如何修订呢?所以统一希腊文词语的中文翻译用词的原则有待商榷。
另外,此次的修订工作也是为了「利于教会圣道礼仪时做出更有效的诵读」。这样做的目的固然高尚,但圣经和与礼仪的关系如胶似漆,不易分离,以同一本圣经译本来达到不同目的(学术性、通俗性、礼仪性),可行性有多大,需要三思。2011年《费肋孟书》和《弟铎书》的修订工作已经结束,但思高圣经学会目前的官网并没有显示「思高圣经」的修订工作及其进度,所以不知道其修订工作何时可以结束。

02 对圣经中文新译本或已有版本
修订工作的几点建议
03 对「共同译本」的展望
房神父在2015年「台湾近代基督教学术研讨会」上演讲时,更是深情回顾与周联华牧师共同翻译圣经30年的美好经历。原来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神学院刚从菲律宾碧瑶搬到现今天主教辅仁大学的隔壁不久,他就想到:「若『思高本圣经』与『和合本圣经』能代表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圣经,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共同译本』圣经的出版呢?」然而,这个想法计划并没有像西方其他语言的大公版本那样顺利。目前我们看到的成果是2015年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的《四福音书-共同译本》。
无法否认,圣经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宝藏。虽然目前在华人世界,各宗派基督徒一起从事翻译释经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挑战,但是「共同译本」依然应是我们共同的企盼。而且,在未来的「共同译本」中,不仅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书目,我们也希望能像TOB那样,加入东正教圣经版本中所多出的书目。如果圣经学者已经意识到,为了解圣经正典的写作背景,需要关注旧约和新约圣经同时代的经外著作,这些东正教圣经所独有的书目(而且是来自《七十贤士译本》)更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
04 数码版本中文圣经
[1]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259页。
[2]虽然亦有不同的声音,但学术界一般还是将此一翻译理论归中国著名的作家与翻译家严复(1854~1921):信,指译文要准确,不增减;达,指译文不拘泥于原文格式;雅,指译文要得体且优雅。而且严复将对「信」的追求放在了首位。参: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80、259页。思高圣经学会在翻译初期也定下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而且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然而在单行本发行结束,准备出版圣经完整本而进行大规模修订时,则改为「信、达、雅」三方面都要兼顾。参:刘赛眉、王敬弘合著,《圣经十讲》(香港:思高圣经学会,2004修订版),78~79页。
[3]参:陈培佳、霍桂泉,〈修订思高圣经译文的经历分享〉,《神思》89期(2011),51~52页。
[4]「我祈求天主,为使你因信德而怀有的慷慨发生功效,使你认清我们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是为基督而行的。」
[5]参:陈培佳、霍桂泉,〈修订思高圣经译文的经历分享〉,53页。
[6]「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
[7]参:陈培佳、霍桂泉,〈修订思高圣经译文的经历分享〉,60页。
[8]举例来说,法文的天主教《官方礼仪圣经译本》(La Bible, Traduction Officielle Liturgique),是由70位译者参与,费时17年,才得以于2013年付梓。
[9]房志荣神父曾提出「意义(或动态)对等」的译法,我认为更适合礼仪上的译本之所需。这样,参与礼仪的人在聆听时比较容易进入圣经语言所表达的意义。
[10]房志荣神父有关「圣经合译委员会」的四次会议记录,分别登载在《神学论集》75期(1988春)和78期(1988冬)。
[11]参:https://krtnews.tw/chinese-church/local/article/default/10805.html
[12]参:黄锡木博士,〈中华圣经译本(1661~1960)数字化工程〉(2019.08.11):https://www.fhl.net/nbg/reading/reading542630.html。


